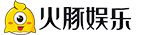在远古巫术时代,先民作歌乐鼓舞以娱诸神。舞蹈曾是一种宗教仪式,具有无穷的神圣意味,而从生物学意义上说,女体天然地是奉献给自然的祭品,在沉浊混沌、粘腻血腥之余,也具有穿越空间和超越自我的力量。我遥想大地之上,河流之畔,初民们的女体献祭之舞,在苍凉乱云的天空之下。祭神歌舞的场所,长满兰草和蘼芜,满眼绿叶白花,芬芳扑鼻。对神而舞的巫女,孔盖兮翠旌,荷衣兮蕙带,一如《楚辞》里的世界的景观。她们不是舞给观众看,她们是舞给神看,所以自有一种尊敬、严肃与端正。巫其实是回到最源头,在阴阳人鬼之间,信仰万物,崇拜自然,祀奉祖先,召请亡魂。
祭神如神在,在每一个值得纪念先人的特殊的日子,尤其在那些一代人受难的事变纪念日,在若干年无数无尽的鲜血流过之后,我们都应该有所祭祀,让牺牲的民族英烈得到敬礼祭拜,也让所有至今飘荡的无名游魂(也许他们中包括了同样横死的敌人),也灭罪消愆,窕冥之中,各安其位,终委顺于天地。

为什么需要祭祀天地人鬼,因为人类从茹毛饮血到刀耕火种,文明和历史在向前发展,可生死存亡的环境又常常迫使人性异化,回归到动物界同类相残甚至同类相食的状态。曾经的暴力,曾经的血腥,曾经的尸陈遍野,曾经的血流成河,受伤者的呼叫,无辜者的呻吟,被饿死的人朝向天空绝望的眼神,所有这些,不可能被一场大雨冲去,一百场倾盆大雨都冲刷不去。在心有余悸的幸存者心中,依然盘桓着无数森森飘荡的幽魂。所有的山水、河流、树木和夜空,所有的道路、通往过去的和朝向未来的,都曾见证过人类的嗜血与滥杀,这一切都需要被抚慰、被平息、被安魂。
在《楚辞·招魂》中兼有仪式主持和呼喊功能的阳巫都是女性,而在后世中的这一职能 都是由男性承担,女性完全退出了这个仪式,可见在中古父权制文化中,男尊女卑的律法导致女性在神圣仪式中的缺席。在去母系氏族时代未远的《楚辞》时代,政教职能分离之后,女性原则上不能过问国家政治,而在宗教仪式中还可以担当主角。《楚辞》中的湘夫人、山鬼、少司命等等,都是芬菲菲兮满堂、来去飘忽的神女,以一腔痴恋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在爱、惑、痛的血河上漂荡一生,这就是女人的天命。终其一生不断流血的女体,是感受性如此丰富的灵体,她们以其自然之舞,献祭于天地,通过以血对血的生存演示,面对着世界的悲剧,用鲜血和生命来承担起其义务,完成补天、济世、安顿人心的义务。

回顾苍茫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前进,有时简直是一种恶的驱动力,从血腥到血腥。有一个成语叫“血流漂杵”,你问我可能吗?血流汇聚成河,长杆兵器都漂了起来。怎么不可能?这样的事,历史上太多太多,就是今天也没断。历史一直很血腥,血流成河,泪流成河,逝者如斯夫!文明就像是一条筑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鲜血是人们相互残杀、偷窃、争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这是凡俗到历史学家根本不想记录的日常生活。历史选择记录的,都是非常态的事件,所以当年鲁迅说翻开中国历史,里面写的都是“吃人”二字,翻开每一页都是血淋淋的历史!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尤其是改朝换代、天崩地裂之际。
历史推进到今天,难道人类就彻底告别暴力了吗?不,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借助科学的力量,人类相互残杀的“效率”也急遽上升。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其战火燃遍全球,而其造成了多少人的死难,造成了多少人的流离失所,造成了多少物质和精神的创伤,那是根本无法用语言能够形容的。而在二十世纪中的那些战争中,除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以外,更是交织着宗教之间、意识形态之间、党派之间、族群之间的各种冲突,其惨烈程度甚至要比世界大战更为血腥。而这样的冲突之中,有多少面带稚气的孩童也拿起了冰冷的刀枪,加入了屠戮的行列。

最真实的东西往往是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所以人们习惯于道貌岸然地站在远处尖叫,满脸上的不屑和惊惶。最大的惊惶其实在他们心里,他们无法面对的那个面目丑陋的自己。这样的一部暴力绵延历史,其实是由每个人或深或浅的参与来完成的。这就是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说的,“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记载着多少的杀戮与战争,而千百年来,又有多少以血洗血,以仇恨唤起更大的仇恨的愚行。在浩瀚的宇宙剧场里,地球只是一个极小的舞台。想想所有那些帝王将相杀戮得血流成河,伴随着杀声四起、哭声连天、箭簇凛冽、枪声密集。他们的辉煌与胜利,曾让他们成为地球这粒悬浮的微尘之上,一个局部转瞬即逝的主宰。是的,可然后呢,不过是转瞬即逝!

不知为什么,常常能够感知到天地之间的某种魂魄不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读多了那些用血泪养育的古歌和神话?在旅顺、在南京、在潼关,在井冈山、在昆仑关、在镇北台,在那些历史上曾经血雨腥风、玉石俱焚的死战之地,山涛云声中静默却永恒的某种冤结压迫,更是让我透不过气来。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些历史时刻的沉重与悲壮,触摸到淤积到暗黑的层层叠叠的血痕。想起被称之为“行吟在青藏高原的屈原”的诗人昌耀,曾有一首诗写过这种感觉:
《仁者》 昌耀
人生困窘
如同在一条
不知首尾的长廊行进
四周都见血迹
仁者之叹不独于
这血的真实
尤在不可畏避的血的义务

这是何等凄怆的歌声,在此诗中,昌耀将泪重重叠叠地向长空弹出,面对杀人如麻、人命如草的历史,“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而昌耀本人的人生,也是何等苦难多舛:参军,负伤,疗养,支援中国西部建设,被划成右派,监禁,劳改,返回城市,写作,成名,生病,坠楼自杀。从诗中能读出当时诗人的心境,可谓内心的真实告白:我们人生常常是困窘的。人生之路就像在一条不知首尾的长廊行进,四周到处都可以看到血迹。一个仁者为什么叹息,他不仅为这个血的真实而叹息,他还要为他的不可回避的血的义务而叹息。血的义务需要仁者来承担,而血的义务也会成就仁者。诗人所能示之于人生的血,只能是自己生命骨髓的耗燃。然而,“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想起莫言在《红高粱家族》的题词中,也写过“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这部小说每一情节都在招魂的总体氛围笼罩下惊心动魄地展开,至《高粱殡》而达到巅峰,《奇死》则是祭奠仪式的尾声。在仪式形式与内容,在基本的招魂功能上,《红高粱家族》和《楚辞·招魂》异曲同工,有着文体风格上诗性的相似。只不过,《楚辞·招魂》召唤的是亡魂,而莫言召唤的是民魂,也即我们血勇顽强的民族精神。《红高粱家族》的故事是莫言祭祀式写作中最具有招魂仪式功能的作品 。
也许这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这是生命伦理的重要价值核心。我也常常能够感受到,这种招魂式写作与祭祀式写作的旷野呼唤,如此骚动不宁,从黑暗中蒸腾,如同搅动了生命平静的一股蛮力。无数的长夜,暗影幢幢从黑暗中来,又冉冉遁失于黑暗之中,催迫着我,要去为人类这条血迹斑斑的辛酸路写一点什么。

本文和图片来自网络,不代表火豚游戏立场,如若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https://www.huotun.com/game/532687.html